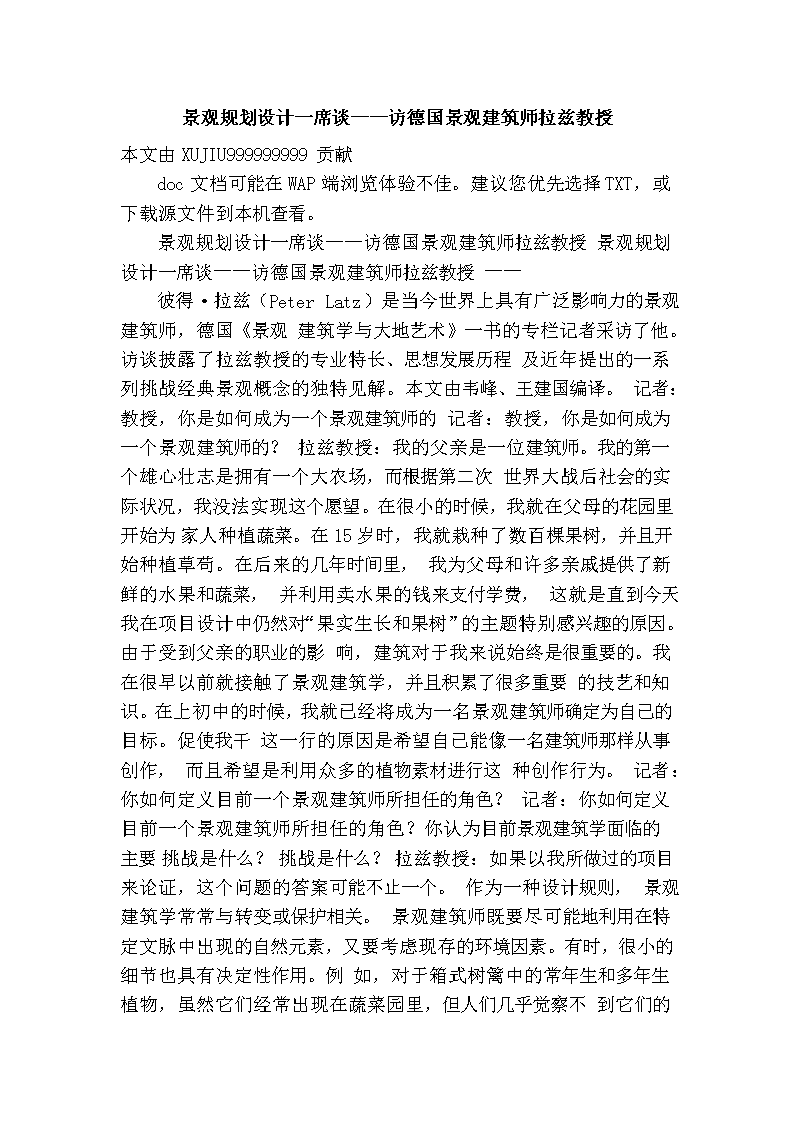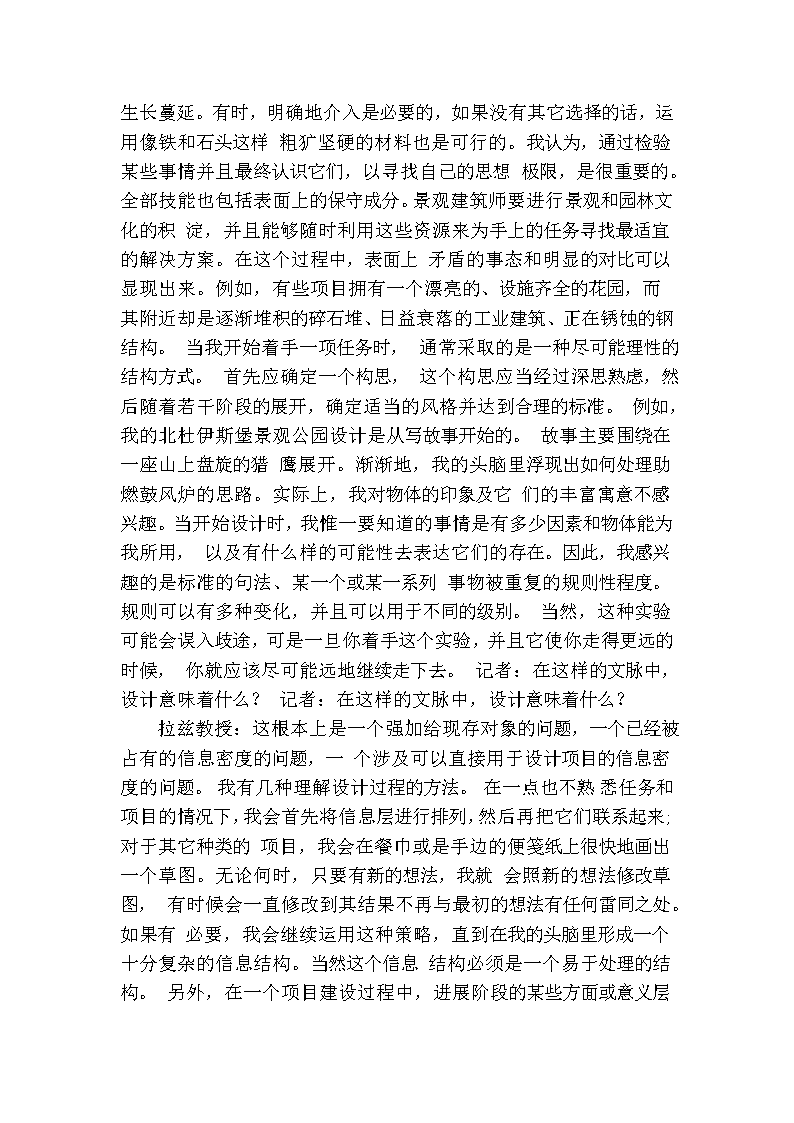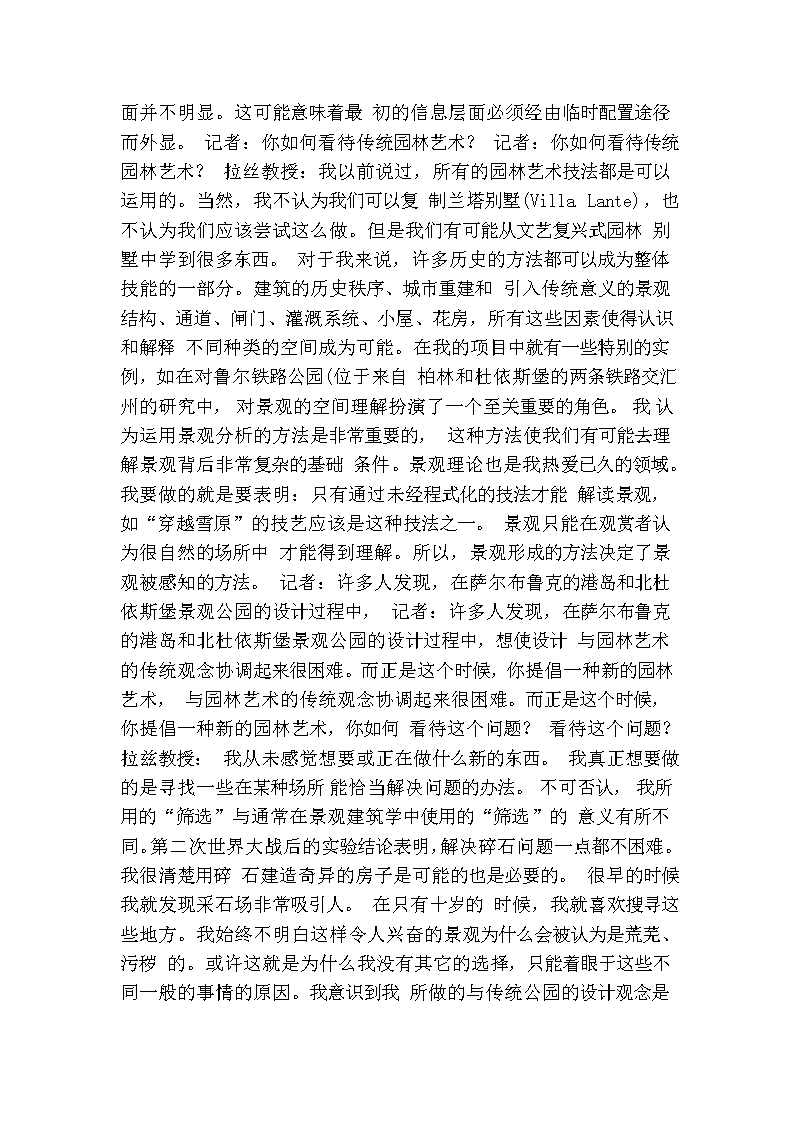- 33.50 KB
- 8页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景观规划设计一席谈——访德国景观建筑师拉兹教授本文由XUJIU999999999贡献doc文档可能在WAP端浏览体验不佳。建议您优先选择TXT,或下载源文件到本机查看。景观规划设计一席谈——访德国景观建筑师拉兹教授景观规划设计一席谈——访德国景观建筑师拉兹教授——彼得·拉兹(PeterLatz)是当今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景观建筑师,德国《景观建筑学与大地艺术》一书的专栏记者采访了他。访谈披露了拉兹教授的专业特长、思想发展历程及近年提出的一系列挑战经典景观概念的独特见解。本文由韦峰、王建国编译。记者:教授,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景观建筑师的记者:教授,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景观建筑师的?拉兹教授:我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我的第一个雄心壮志是拥有一个大农场,而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的实际状况,我没法实现这个愿望。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父母的花园里开始为家人种植蔬菜。在15岁时,我就栽种了数百棵果树,并且开始种植草苟。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为父母和许多亲戚提供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利用卖水果的钱来支付学费,这就是直到今天我在项目设计中仍然对“果实生长和果树”的主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由于受到父亲的职业的影响,建筑对于我来说始终是很重要的。我在很早以前就接触了景观建筑学,并且积累了很多重要的技艺和知识。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将成为一名景观建筑师确定为自己的目标。促使我干这一行的原因是希望自己能像一名建筑师那样从事创作,而且希望是利用众多的植物素材进行这种创作行为。记者:你如何定义目前一个景观建筑师所担任的角色?记者:你如何定义目前一个景观建筑师所担任的角色?你认为目前景观建筑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拉兹教授:如果以我所做过的项目来论证,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作为一种设计规则,景观建筑学常常与转变或保护相关。景观建筑师既要尽可能地利用在特定文脉中出现的自然元素,又要考虑现存的环境因素。有时,很小的细节也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对于箱式树篱中的常年生和多年生植物,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蔬菜园里,但人们几乎觉察不
到它们的生长蔓延。有时,明确地介入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其它选择的话,运用像铁和石头这样粗犷坚硬的材料也是可行的。我认为,通过检验某些事情并且最终认识它们,以寻找自己的思想极限,是很重要的。全部技能也包括表面上的保守成分。景观建筑师要进行景观和园林文化的积淀,并且能够随时利用这些资源来为手上的任务寻找最适宜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矛盾的事态和明显的对比可以显现出来。例如,有些项目拥有一个漂亮的、设施齐全的花园,而其附近却是逐渐堆积的碎石堆、日益衰落的工业建筑、正在锈蚀的钢结构。当我开始着手一项任务时,通常采取的是一种尽可能理性的结构方式。首先应确定一个构思,这个构思应当经过深思熟虑,然后随着若干阶段的展开,确定适当的风格并达到合理的标准。例如,我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设计是从写故事开始的。故事主要围绕在一座山上盘旋的猎鹰展开。渐渐地,我的头脑里浮现出如何处理助燃鼓风炉的思路。实际上,我对物体的印象及它们的丰富寓意不感兴趣。当开始设计时,我惟一要知道的事情是有多少因素和物体能为我所用,以及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去表达它们的存在。因此,我感兴趣的是标准的句法、某一个或某一系列事物被重复的规则性程度。规则可以有多种变化,并且可以用于不同的级别。当然,这种实验可能会误入歧途,可是一旦你着手这个实验,并且它使你走得更远的时候,你就应该尽可能远地继续走下去。记者:在这样的文脉中,设计意味着什么?记者:在这样的文脉中,设计意味着什么?拉兹教授:这根本上是一个强加给现存对象的问题,一个已经被占有的信息密度的问题,一个涉及可以直接用于设计项目的信息密度的问题。我有几种理解设计过程的方法。在一点也不熟悉任务和项目的情况下,我会首先将信息层进行排列,然后再把它们联系起来;对于其它种类的项目,我会在餐巾或是手边的便笺纸上很快地画出一个草图。无论何时,只要有新的想法,我就会照新的想法修改草图,有时候会一直修改到其结果不再与最初的想法有任何雷同之处。如果有必要,我会继续运用这种策略,直到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一个十分复杂的信息结构。当然这个信息结构必须是一个易于处理的结构。
另外,在一个项目建设过程中,进展阶段的某些方面或意义层面并不明显。这可能意味着最初的信息层面必须经由临时配置途径而外显。记者:你如何看待传统园林艺术?记者:你如何看待传统园林艺术?拉丝教授:我以前说过,所有的园林艺术技法都是可以运用的。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复制兰塔别墅(VillaLante),也不认为我们应该尝试这么做。但是我们有可能从文艺复兴式园林别墅中学到很多东西。对于我来说,许多历史的方法都可以成为整体技能的一部分。建筑的历史秩序、城市重建和引入传统意义的景观结构、通道、闸门、灌溉系统、小屋、花房,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认识和解释不同种类的空间成为可能。在我的项目中就有一些特别的实例,如在对鲁尔铁路公园(位于来自柏林和杜依斯堡的两条铁路交汇州的研究中,对景观的空间理解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运用景观分析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去理解景观背后非常复杂的基础条件。景观理论也是我热爱已久的领域。我要做的就是要表明:只有通过未经程式化的技法才能解读景观,如“穿越雪原”的技艺应该是这种技法之一。景观只能在观赏者认为很自然的场所中才能得到理解。所以,景观形成的方法决定了景观被感知的方法。记者:许多人发现,在萨尔布鲁克的港岛和北杜依斯堡景观公园的设计过程中,记者:许多人发现,在萨尔布鲁克的港岛和北杜依斯堡景观公园的设计过程中,想使设计与园林艺术的传统观念协调起来很困难。而正是这个时候,你提倡一种新的园林艺术,与园林艺术的传统观念协调起来很困难。而正是这个时候,你提倡一种新的园林艺术,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看待这个问题?拉兹教授:我从未感觉想要或正在做什么新的东西。我真正想要做的是寻找一些在某种场所能恰当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可否认,我所用的“筛选”与通常在景观建筑学中使用的“筛选”的意义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验结论表明,解决碎石问题一点都不困难。我很清楚用碎石建造奇异的房子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采石场非常吸引人。在只有十岁的时候,我就喜欢搜寻这些地方。我始终不明白这样令人兴奋的景观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荒芜、污秽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着眼于这些不同一般的事情的原因。我意识到我
所做的与传统公园的设计观念是不一致的,它具有一定的冲击力。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来自一些同事的强烈反对却是我始料未及的。记者: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挑衅或者对理解习惯的违背?记者: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挑衅或者对理解习惯的违背?者对理解习惯的违背拉兹教授:我是有意识地进行与一般习惯不同的尝试,主要是想寻找那些有特色的地方,或许只想表达什么是新概念。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密斯的建筑很感兴趣,尤其是他所关注的信息的简约和冗余问题。我总是着迷于简单性设计和景观中的加法设计。所以,对于我来说,在萨尔布鲁克港岛用网格将公园划分处理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理性的方法已经表达在平面图中。我或许能发明出另一种网格,不过目前还没有具体想法。记者: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你众多迷人的作品中有两个项目是直接建在废墟上的。记者: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你众多迷人的作品中有两个项目是直接建在废墟上的。拉兹教授:当然,我努力寻找景观中美的成分并且欣赏它们。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想象力在哪里,是在协调中还是在冲突中?冲突可能产生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协调及不同的和谐。如果你来自像萨尔岛这样的丘陵地区,那么像采石场这样不寻常的现象自然就会令你激动不已。我不像其它地方的人们那样,至今对二战的一些遗迹仍然有所忌讳。我将一个在二战时被炸毁的碉堡保持原样,这些废墟般的场所不仅为景观建筑师,更重要的是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吸引到这里的原因。记者: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对敬畏的迷恋和对废墟美的喜好,记者: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对敬畏的迷恋和对废墟美的喜好,这似乎更像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对废墟美的喜好观点。观点。拉兹教授:最近,我在德累斯顿作了一个演讲,提倡“从废墟到废墟的保护”。表面上,偶然性导致了人类的冲突,因此它通常被认为是消极的,但我认为它也有非常令人兴奋和积极的一面,进一步看,保护废墟其实是对保护自然的贡献。这些场所为不同事态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我并非刻意追求某一流派。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其它人文思潮各有其作用,相信它们可以同时存在。所以,不能严格区分理性和浪漫。我可以按理性的准则建一幢木头房子,当一缕阳光透过玻璃屋顶照射进来时,
因偶然性的出现而产生了一幅意想不到的浪漫景象。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也可以有意创造其它浪漫景象。对我来说,事情的发展存在一种预先确定的,在思想、情感和经验上的预演模式。例如,当要去海边时,我基本上提前几周就已经知道在那里能获得什么样的经历。我已经说过,我对语义的作用根本不感兴趣。对我来说,语义的作用远不如找到一种结构重要。在这种结构里,大量的语义可以主动地互相转变,正如季节、天气和事件的变换可以随时改变其自身表达的模式一样。记者:年你提出“重新理解自然的时代已经来到”你如何定义你的自然概念,记者:1993年你提出“重新理解自然的时代已经来到”。你如何定义你的自然概念,在你的设计中可以看到相关特征吗?的设计中可以看到相关特征吗?拉兹教授:一般来说,理解自然的方法与理解任何其它文化形式的方法一样多种多样。当前,我们通过人文景观理解自然的方法已经很清楚了。这种所谓的人文景观事实上是一种残酷的实用性景观,已经被农业和林业长期开发。我在演讲和文章中想要论述的是对自然的一般性理解,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刺激性的计划。这不仅仅是我个人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尽管我并不都是成功的,但我想尽量把景观和自然的区别搞清楚,原因是事实上它们彼此没有多大的关系。景观是个人文概念,更确切地说,是被人类社会所珍爱的事物,而自然是一种自律、一种神话。我们基本上都身处自然之中,一旦我们经历了肉体上的痛苦之后,某些东西又变得可亲可爱了。在很多情况下,令人着迷的是(生态)系统,一方面它必须满足极高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它自身要发展出理想的生态状态。如果生态系统不再运转,生态的外观将不复存在。我刚才所描述的是一个同步过程。这个同步过程按规则应以一种辨证的关系来理解。然而,我发现同步的方面更有趣。当然,虽然我喜欢五月里被鲜花和草地簇拥着的房子,但是对自然和景观进行实验是我们的职责,哪怕仅仅是在头脑中的观念。把这些经验应用到实践中的结果是可以获得巨大的收获,确定的价值也因此即刻被转移。我可以想象出一个完全用生锈的螺丝钉做成的花床基础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可以想象在一个60cm厚的混合肥料基上茁壮生长的萝卜、生菜
和南瓜的样子。这是园丁特有的感觉。这很可能使一个现有的人造景观变得迷人,并且使之成为一个典型的景观片段,被人认可。在20世纪20年代,这很可能根本不被重视,但如今却令人非常兴奋。我们总认为世界上除了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原始森林外,已经没有什么遗产了,甚至现在我们想上月球去搜寻一下。然而,最迷人的且最易开发的地方恰好就在我们的城市中。我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这些地方再走近一点。另一个刺激的想法是—我想创作一个没有任何树和灌木的公园。这意昧着我们必须努力不持陈见,走出迁腐。例如,试图用植被覆盖矿渣堆就是可笑的。对待这种材料堆积物,惟一的自然原则是应当允许一种适当的侵蚀行为发生,这一行为过程完全可以使这种材料堆积物产生新的构成。有趣的是我们应该促使和鼓励这种侵蚀发生,然后利用变化后的新奇结构来表述环境,而非一概而论的只是保护。同样的措施也正在德国其它州被用来复育废弃的煤矿。在复育过程中,设计者总希望形成一种技术美学意义上的形象,但这通常会引起人们的厌烦,而且以后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维护其状态上。“侵蚀”在其它场合里的确是件糟糕的事,而对于我来说却是很重要的。举一个金属广场(PiazzaMetallica)的例子,这个厚重的直角铁盘源自两个有趣的物理过程:一个是形成坚硬金属的过程,曾经被一层矿渣覆盖着,很难暴露出来;另一个是侵蚀过程。广场被描述为一种技术和一个历史时段,这里不是用水,而是将13000摄氏度的高温铸铁熔液倒进这个盘子,创造了类似冰川断口的河流系统。换言之,原始的构成通过熔铸原理的力量得以形成。作为自然的象征,我发现这比几棵被遗弃的白桦树更能激发我无穷的兴趣。记者:你如何表述景观建筑学至少比艺术晚20年产生的原因?艺术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灵感?年产生的原因?艺术可以提供什么样的灵感?记者:我假定简单模仿艺术模式是不成问题的。我假定简单模仿艺术模式是不成问题的。拉兹教授:除了个别例子外,有关园林设计真正与现代主义对话的范例几乎没有。多数的尝试只是停留在表面效果,在园林设计中从来没有一个具有真正说服力的包含大众文化的实例。尽管结构主义原则特别适合景观结构的交通组织,但几乎没有人认真考虑过结构主义的观点。少数
可行的美学原则尝试考虑经济原则。我没有谈论类似园林模式的产品和它们特殊的组织形式,我谈论的完全是一种不同于园林设计的表现尺度。通常,我们的职业习惯是喜欢玩设计游戏,或者深入研究过去的设计,或许这可以通过媒体世界的机器设备来解释。大多数景观建筑师都没有勇气使用当代文化语言。而同时代的艺术和建筑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学会面对这些问题。记者:你将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地貌部分解读为“大地艺术”这令人很惊奇。记者:你将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地貌部分解读为“大地艺术”,这令人很惊奇。为什么你要使用一个明显属于艺术范畴的术语?要使用一个明显属于艺术范畴的术语?拉兹教授:“铁路竖琴”实际上是铁路线的一个交汇处。这里每一个二级轨道都通向下方,一级轨道从中间通向上方,是一个充分运用了科技的奇妙作品。铁路轨道线有规律的分合形成了敏感的形态,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很快就发现了北杜依斯堡的铁路公园。铁道轨迹所带来的动感有如芭蕾般令人眼花缭乱。设计这个铁路设施的工程师们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六七十年),当然靠的是技术而不是艺术。如果当时告诉他们正在做的是艺术,那反而可能起到消极的作用,甚至使他们的工作白费。技术史中常常会出现令人着迷的结构,它们的表现力应该得到公认和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并没有艺术家参与,我使用“大地艺术”这一术语的原因。在许多物品中,品质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文明中的矛盾问题之一就是这样的创造是否算技术,矿渣堆是否包括在这个范畴里,是否也应该当成人文纪念碑来保护。记者: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长远的发展计划中包括了逐渐增加艺术方面的内容。记者:埃姆歇公园国际建筑展长远的发展计划中包括了逐渐增加艺术方面的内容。你在这方面的观点是什么?方面的观点是什么?拉兹教授:我深信园林艺术是存在的。在我没有真正提出园林艺术是什么的时候,不管我曾经做的项目是否被划归此类,我都希望它们属于园林艺术。不管大部分作品的功能如何,我感觉在我作品中的确存在一部分不能仅从使用价值来判定的东西,因为它们还传递着其它更深的涵
义。当我寻求对场所、空间和情景的明确解读时,各种各样的文化语言都可以被使用,而艺术语言也是其中之一。在建筑史的研究者一直都在寻找建筑技术、文明遗产、艺术遗产、神学意义等的客观标准时,尽管我们的文明一直被认为是由彼此分离的部分所构成,但我还是感觉区分艺术、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之间的差别很可能真的没有太多的意义。[注释]①本文编译自彼得·拉兹所著的《景观句法》一文,原文有些地方比较晦涩,考虑到便于读者理解及杂志篇幅所限,译者在不影响文章顺序和意思的前提下做了局部编辑和删节。原文可参见PeterLatz.TheSyntaxofLandscape,UdoWelacher,BetweenLandscapeArchitectureandLandArt[M].Birkhauser,1999.121-136.[译者简介]韦峰,男,郑州大学建筑学院教师。王建国,男,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圳立委员会等韦平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委员会副主任,《规划师》编委。1'
您可能关注的文档
- 郑州人民公园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调研报告
- 同济大学景观规划设计原理课程讲义5-带状景观规划设计
- 南京栖霞商务区二期景观规划设计任务书
- 城北新区主路网两侧绿化退让内景观规划设计项目中标公示
- 《景观规划设计师》复习题
- 景观规划设计笔记
- 临沂市沂河滨水景观规划设计研究.doc
- 宜昌市城市生态景观规划设计任务书
- 广安市兔儿山公园景观规划设计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 临清古运河文化广场景观规划设计
- 南宁市某片区景观规划设计报告
- 景观规划设计原理笔记
- 景观规划设计术语
- 浅谈我国田园生态景观规划设计
- 观光休闲农业园区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 浅谈我国田园生态景观规划设计
- 滨水广场景观规划设计
- 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