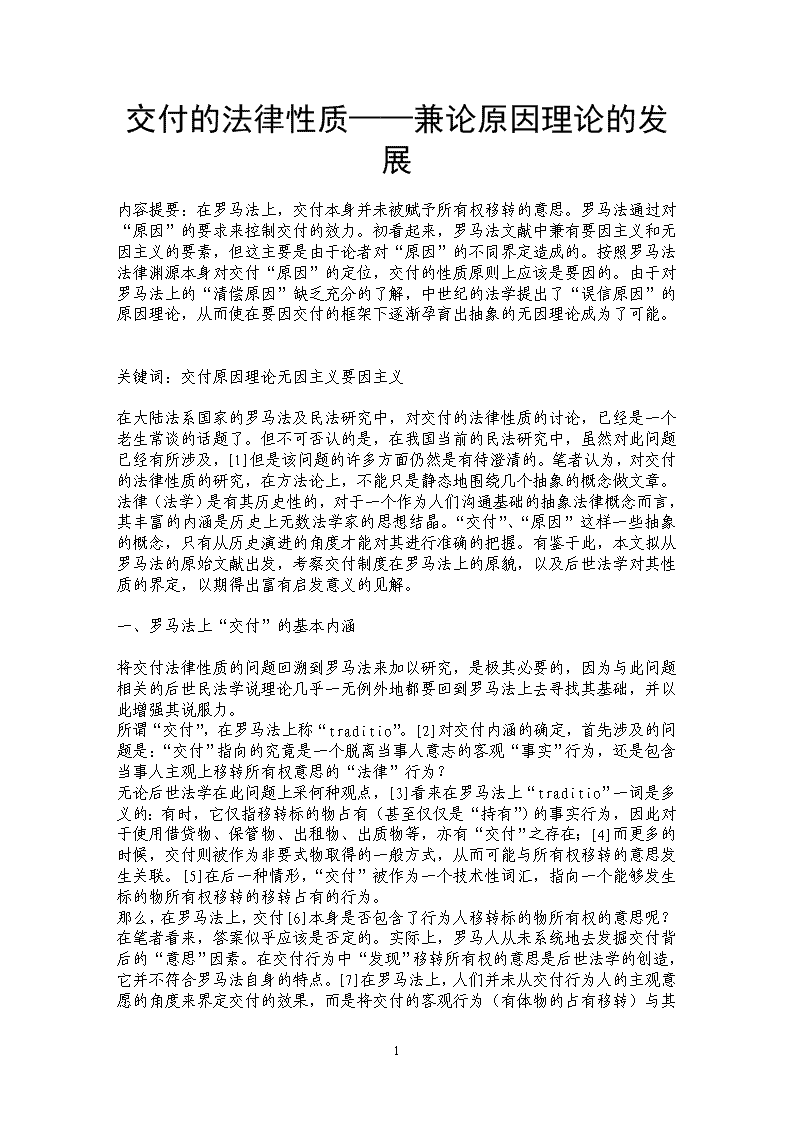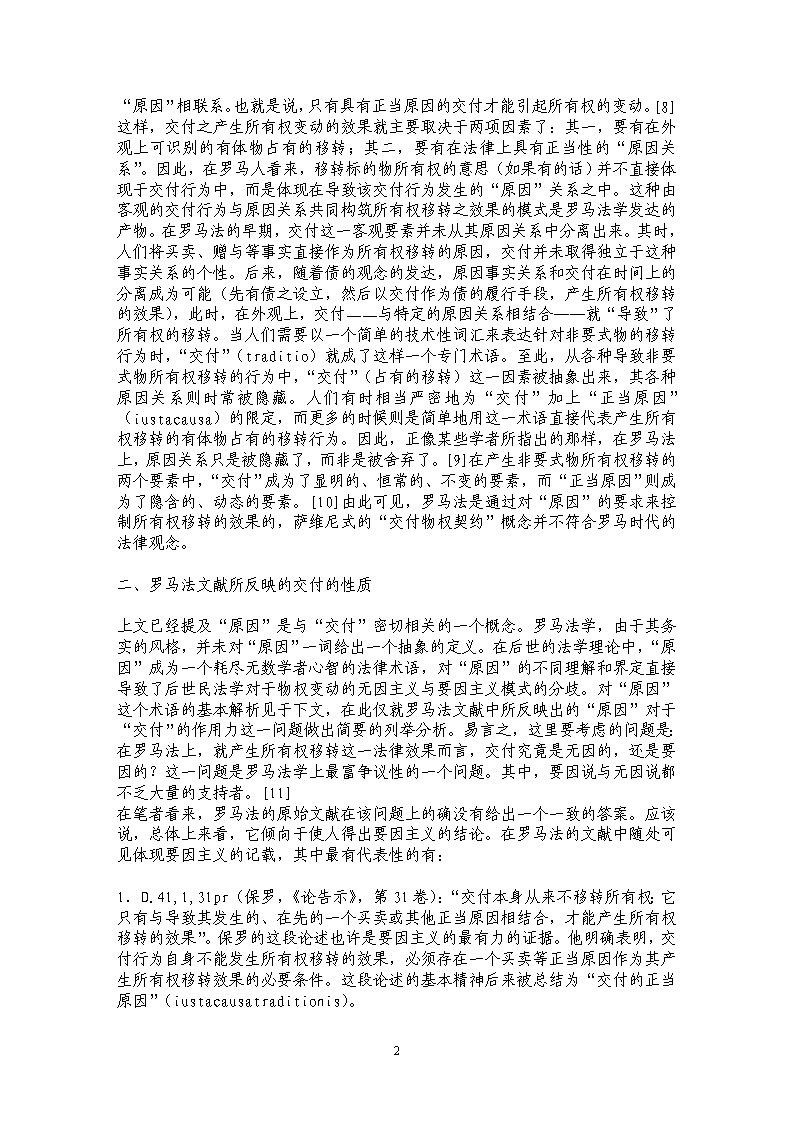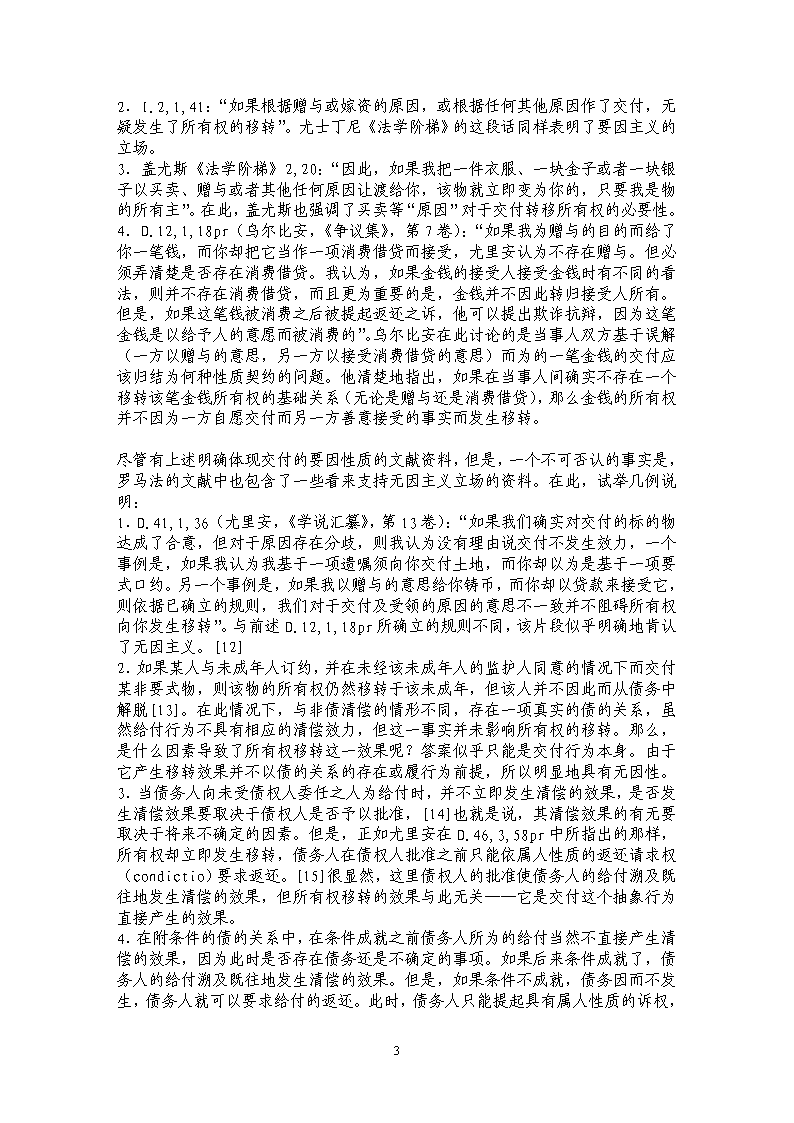- 62.00 KB
- 14页
- 1、本文档共5页,可阅读全部内容。
- 2、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内容提供方所有。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可选择认领,认领后既往收益都归您。
- 3、本文档由用户上传,本站不保证质量和数量令人满意,可能有诸多瑕疵,付费之前,请仔细先通过免费阅读内容等途径辨别内容交易风险。如存在严重挂羊头卖狗肉之情形,可联系本站下载客服投诉处理。
- 文档侵权举报电话:19940600175。
交付的法律性质——兼论原因理论的发展内容提要:在罗马法上,交付本身并未被赋予所有权移转的意思。罗马法通过对“原因”的要求来控制交付的效力。初看起来,罗马法文献中兼有要因主义和无因主义的要素,但这主要是由于论者对“原因”的不同界定造成的。按照罗马法法律渊源本身对交付“原因”的定位,交付的性质原则上应该是要因的。由于对罗马法上的“清偿原因”缺乏充分的了解,中世纪的法学提出了“误信原因”的原因理论,从而使在要因交付的框架下逐渐孕育出抽象的无因理论成为了可能。关键词:交付原因理论无因主义要因主义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罗马法及民法研究中,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讨论,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当前的民法研究中,虽然对此问题已经有所涉及,[1]但是该问题的许多方面仍然是有待澄清的。笔者认为,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只是静态地围绕几个抽象的概念做文章。法律(法学)是有其历史性的,对于一个作为人们沟通基础的抽象法律概念而言,其丰富的内涵是历史上无数法学家的思想结晶。“交付”、“原因”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只有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罗马法的原始文献出发,考察交付制度在罗马法上的原貌,以及后世法学对其性质的界定,以期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一、罗马法上“交付”的基本内涵将交付法律性质的问题回溯到罗马法来加以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与此问题相关的后世民法学说理论几乎一无例外地都要回到罗马法上去寻找其基础,并以此增强其说服力。所谓“交付”,在罗马法上称“traditio”。[2]对交付内涵的确定,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交付”指向的究竟是一个脱离当事人意志的客观“事实”行为,还是包含当事人主观上移转所有权意思的“法律”行为?无论后世法学在此问题上采何种观点,[3]看来在罗马法上“traditio”一词是多义的:有时,它仅指移转标的物占有(甚至仅仅是“持有”)的事实行为,因此对于使用借贷物、保管物、出租物、出质物等,亦有“交付”之存在;[4]而更多的时候,交付则被作为非要式物取得的一般方式,从而可能与所有权移转的意思发生关联。[5]在后一种情形,“交付”被作为一个技术性词汇,指向一个能够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移转占有的行为。那么,在罗马法上,交付[6]本身是否包含了行为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呢?在笔者看来,答案似乎应该是否定的。实际上,罗马人从未系统地去发掘交付背后的“意思”因素。在交付行为中“发现”移转所有权的意思是后世法学的创造,它并不符合罗马法自身的特点。[7]在罗马法上,人们并未从交付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角度来界定交付的效果,而是将交付的客观行为(有体物的占有移转)与其14
“原因”相联系。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正当原因的交付才能引起所有权的变动。[8]这样,交付之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效果就主要取决于两项因素了:其一,要有在外观上可识别的有体物占有的移转;其二,要有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的“原因关系”。因此,在罗马人看来,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如果有的话)并不直接体现于交付行为中,而是体现在导致该交付行为发生的“原因”关系之中。这种由客观的交付行为与原因关系共同构筑所有权移转之效果的模式是罗马法学发达的产物。在罗马法的早期,交付这一客观要素并未从其原因关系中分离出来。其时,人们将买卖、赠与等事实直接作为所有权移转的原因,交付并未取得独立于这种事实关系的个性。后来,随着债的观念的发达,原因事实关系和交付在时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先有债之设立,然后以交付作为债的履行手段,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此时,在外观上,交付――与特定的原因关系相结合——就“导致”了所有权的移转。当人们需要以一个简单的技术性词汇来表达针对非要式物的移转行为时,“交付”(traditio)就成了这样一个专门术语。至此,从各种导致非要式物所有权移转的行为中,“交付”(占有的移转)这一因素被抽象出来,其各种原因关系则时常被隐藏。人们有时相当严密地为“交付”加上“正当原因”(iustacausa)的限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简单地用这一术语直接代表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有体物占有的移转行为。因此,正像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罗马法上,原因关系只是被隐藏了,而非是被舍弃了。[9]在产生非要式物所有权移转的两个要素中,“交付”成为了显明的、恒常的、不变的要素,而“正当原因”则成为了隐含的、动态的要素。[10]由此可见,罗马法是通过对“原因”的要求来控制所有权移转的效果的,萨维尼式的“交付物权契约”概念并不符合罗马时代的法律观念。二、罗马法文献所反映的交付的性质上文已经提及“原因”是与“交付”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罗马法学,由于其务实的风格,并未对“原因”一词给出一个抽象的定义。在后世的法学理论中,“原因”成为一个耗尽无数学者心智的法律术语,对“原因”的不同理解和界定直接导致了后世民法学对于物权变动的无因主义与要因主义模式的分歧。对“原因”这个术语的基本解析见于下文,在此仅就罗马法文献中所反映出的“原因”对于“交付”的作用力这一问题做出简要的列举分析。易言之,这里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罗马法上,就产生所有权移转这一法律效果而言,交付究竟是无因的,还是要因的?这一问题是罗马法学上最富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其中,要因说与无因说都不乏大量的支持者。[11]在笔者看来,罗马法的原始文献在该问题上的确没有给出一个一致的答案。应该说,总体上来看,它倾向于使人得出要因主义的结论。在罗马法的文献中随处可见体现要因主义的记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1.D.41,1,31pr(保罗,《论告示》,第31卷):“交付本身从来不移转所有权:它只有与导致其发生的、在先的一个买卖或其他正当原因相结合,才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保罗的这段论述也许是要因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他明确表明,交付行为自身不能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必须存在一个买卖等正当原因作为其产生所有权移转效果的必要条件。这段论述的基本精神后来被总结为“交付的正当原因”(iustacausatraditionis)。14
2.I.2,1,41:“如果根据赠与或嫁资的原因,或根据任何其他原因作了交付,无疑发生了所有权的移转”。尤士丁尼《法学阶梯》的这段话同样表明了要因主义的立场。3.盖尤斯《法学阶梯》2,20:“因此,如果我把一件衣服、一块金子或者一块银子以买卖、赠与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让渡给你,该物就立即变为你的,只要我是物的所有主”。在此,盖尤斯也强调了买卖等“原因”对于交付转移所有权的必要性。4.D.12,1,18pr(乌尔比安,《争议集》,第7卷):“如果我为赠与的目的而给了你一笔钱,而你却把它当作一项消费借贷而接受,尤里安认为不存在赠与。但必须弄清楚是否存在消费借贷。我认为,如果金钱的接受人接受金钱时有不同的看法,则并不存在消费借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金钱并不因此转归接受人所有。但是,如果这笔钱被消费之后被提起返还之诉,他可以提出欺诈抗辩,因为这笔金钱是以给予人的意愿而被消费的”。乌尔比安在此讨论的是当事人双方基于误解(一方以赠与的意思,另一方以接受消费借贷的意思)而为的一笔金钱的交付应该归结为何种性质契约的问题。他清楚地指出,如果在当事人间确实不存在一个移转该笔金钱所有权的基础关系(无论是赠与还是消费借贷),那么金钱的所有权并不因为一方自愿交付而另一方善意接受的事实而发生移转。尽管有上述明确体现交付的要因性质的文献资料,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罗马法的文献中也包含了一些看来支持无因主义立场的资料。在此,试举几例说明:1.D.41,1,36(尤里安,《学说汇纂》,第13卷):“如果我们确实对交付的标的物达成了合意,但对于原因存在分歧,则我认为没有理由说交付不发生效力,一个事例是,如果我认为我基于一项遗嘱须向你交付土地,而你却以为是基于一项要式口约。另一个事例是,如果我以赠与的意思给你铸币,而你却以贷款来接受它,则依据已确立的规则,我们对于交付及受领的原因的意思不一致并不阻碍所有权向你发生移转”。与前述D.12,1,18pr所确立的规则不同,该片段似乎明确地肯认了无因主义。[12]2.如果某人与未成年人订约,并在未经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而交付某非要式物,则该物的所有权仍然移转于该未成年,但该人并不因此而从债务中解脱[13]。在此情况下,与非债清偿的情形不同,存在一项真实的债的关系,虽然给付行为不具有相应的清偿效力,但这一事实并未影响所有权的移转。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所有权移转这一效果呢?答案似乎只能是交付行为本身。由于它产生移转效果并不以债的关系的存在或履行为前提,所以明显地具有无因性。3.当债务人向未受债权人委任之人为给付时,并不立即发生清偿的效果,是否发生清偿效果要取决于债权人是否予以批准,[14]也就是说,其清偿效果的有无要取决于将来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正如尤里安在D.46,3,58pr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权却立即发生移转,债务人在债权人批准之前只能依属人性质的返还请求权(condictio)要求返还。[15]很显然,这里债权人的批准使债务人的给付溯及既往地发生清偿的效果,但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与此无关——它是交付这个抽象行为直接产生的效果。14
4.在附条件的债的关系中,在条件成就之前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当然不直接产生清偿的效果,因为此时是否存在债务还是不确定的事项。如果后来条件成就了,债务人的给付溯及既往地发生清偿的效果。但是,如果条件不成就,债务因而不发生,债务人就可以要求给付的返还。此时,债务人只能提起具有属人性质的诉权,这表明标的物的所有权已因交付而发生了移转。[16]这显然也体现了交付对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无因性。[17]5.罗马法中体现无因主义的具体规则还包括一大类被称为“具有特定目的的给予”(Datioobrem)的情形。所谓“具有特定目的的给予”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当事人间的这种关系不被视为市民法上的一类契约,[18]所以不受契约法上的诉权保护;其次,当事人一方为将来的某个目的而向另一方移转某物的所有权。[19]这个目的可以构成对方的一个对待给付,也可以不是;这个目的可以是为市民法所承认的(如负担赠与、死因赠与等),也可以不为市民法承认(如“以获得对方的给而给doutdes”、“以获得对方的为而给doutfacias”等),甚至还可以是为市民法所禁止的(如所谓“为不道德目的的给予”)。在所有上述情形,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仅因交付而发生,即使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当事人未达到其预定的目的,也不能主张标的物所有权尚未发生移转——实际上他仅受具有对人诉讼性质的返还之诉condictio的保护。例如:(1)在婚姻缔结之前设立嫁资,尽管嫁资的设立是以婚姻的缔结为其目的,但是,嫁资的所有权仍然在缔结婚姻之前就因交付而发生了移转。如果后来婚姻未缔结,那么嫁资设立人也仅能依以嫁资为原因的不当得利诉权(condictioobcausamdatorum)请求予以返还。嫁资设立人所获得的此项诉权表明嫁资所有权的移转并非以婚姻的存在为其法律要件,而且嫁资所有权的移转甚至并不以婚姻的缔结为其延缓条件,也就是说,除非当事人明确做出了所有权保留的约定,嫁资的所有权在婚姻缔结之前就立即因交付而发生了移转。这显然表明嫁资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不受婚姻这个“原因”关系的牵连,在性质上嫁资的交付应该属于抽象行为。[20](2)所谓“诚信的给予”(datioobremhonestam)并不构成市民法承认的契约关系,它并非以积极的方式来规范当事人间的关系,其作用方式是消极的。举例来说,如果当事人间达成“我提兹给你100元,你解放奴隶史蒂古”的合意,由于该合意不属于任何契约的类型,因而,支付了100元的提兹并不能够诉请对方当事人做出对待给付。实际上,他所可能获得的保护只是在对方不解放奴隶时要求所支付的100元金钱的返还。因此,这种关系受不当得利制度而非不履行契约制度的调整。[21]这样,在双方达成合意而且提兹已将100元交付给对方当事人之后,后者并不立即产生做出对待给付的债务:是否解放奴隶完全取决于接受了金钱之人的意愿,在其不履行时,他仅负有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因此,如果提兹交付金钱的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那么该笔金钱的所有权在对方不为对待给付义务时就不应发生移转,因为正是对方的对待给付构成了移转的原因。然而,我们从罗马法的文献中看到,在此情形,提兹所能主张的诉权毫无疑问地是对人性的condictio,而非对物性的vindicatio。所以,我们只能得出提兹的交付行为系无因的移转行为的结论。(3)即使是在所谓“为不道德目的的给予”关系中,尽管所有权移转的目的(即其“原因”)不为法律所认可(例如,在无偿寄托关系中,受寄人本应无条件地归还寄托物,但却以不归还寄托物为要挟使寄托人向其支付一笔金钱),但是,通过交付行为做出给付的人在事后并不能主张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之诉,而只能根据对人性的请求返还之诉(condictioobturpencausam)要求利益的返还。如果说标的物的所有权在目的非法的情况下仍然发生移转,那么很显然,移转标的物的行为应该是一个其效力不受原因关系影响的抽象行为。三、无因和要因理论差异的基本分析14
如上文所示,罗马法的文献似乎为要因论者和无因论者都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论据。[22]那么,如何对这一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呢?事实上,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总是会透过对罗马法文献记载内容的“解释”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否认对立的观点。如上所述,从总体上看,罗马法文献似乎更倾向于交付移转所有权的要因性质,但无因论者确也能够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来消除“原因”的作用力。例如,无因论者不仅要应对保罗在D.41,1,31pr中对“正当原因”的一般要求,而且也要对一些看来体现了要因主义的具体规则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后者而言,一个事例是:根据古罗马的一项法律(LexIulia),夫妻之间的赠与是无效的,与此规则相对应,夫妻间以赠与为目的的标的物的交付不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显然,此项规则似乎体现了要因主义,因为如果夫妻间的交付行为是抽象行为的话,那么,尽管原因不合法,所有权仍应发生移转。有意思的是,无因论者在此运用了德国法学限制无因主义效力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方法——共同瑕疵理论:有学者提出,在诸如夫妻间互相赠与等违反法律的场合,违法性不仅打击原因关系,而且也直接影响抽象行为的效力,因此,所有权移转效果的阻却并非由于没有恰当的原因关系的支持,而是由于抽象行为本身被认为具有了违法性。[23]对于前者,也就是说,体现要因主义一般规则的保罗的论述,要将其与无因主义相协调似乎要更困难一些。无因论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将罗马人所谓的“原因”主观化,也就是说,不以某个客观存在的产生所有权移转义务的法律关系作为原因,而是将原因解释为当事人具有的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将保罗对买卖和其他“正当原因”的强调解释为不过是为了表明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的必要性。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将“原因”的概念转换成“动机”,这样,在这种原因意义上的所谓“要因行为”实际上就进入了无因行为的范畴。在笔者看来,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上,试图从罗马法的文献中揭示“原本意义上的”罗马法上交付的性质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罗马法是一个重具体轻抽象、重实践轻理论的法律体系。在古罗马时代,“原因”、“交付”、“契约”、“所有权”这些概念都未得到高度的抽象,古罗马的法学家关注的是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抽象的体系建构。实际上,鉴于罗马法学的务实性,法学家们并未超越具体情况下可以行使的诉权(对物性的vindicatio抑或是对人性的condictio)而去抽象地探讨所有权移转的要因主义或无因主义的规则。而且,作为法律渊源的法学家意见相互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试图从文献中得出一个贯彻始终的观点事实上是不可能的。[24]当然,前述观念并不影响人们从罗马法文献中发现交付法律性质的一般原则(在与“例外”相对的意义上而言),然而,在考察学者们对此问题所做出的大相径庭的分析时,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谓“要因”与“无因”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者们对“原因”的不同界定做造成的。时常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罗马法文献中的同一个片断,要因论者和无因论者都以其为论据。以所谓Datioobrem为例,如前文所述,不少学者以其作为无因主义的论据,但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却以此作为要因主义的论据。两者论证的差异在于:前者只将产生给付义务的一个法律关系视为原因;而后者则认为原因既可以是一个产生给付义务的契约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同时也可以仅是某个驱动当事人完成交付的动因。[25]因此,一个明显的,但往往却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事实是,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讨论——无论是罗马法意义上的还是现代法意义上的——取决于人们对“原因”的界定。14
四、原因理论的演进:走向无因主义对原因理论的演进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后世学者们对罗马法文献中关于“交付的正当原因”(iustacausatraditionis)的记载的解释。如前文所述,有关产生所有权移转效力的交付需要具有正当原因的一般性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保罗在D.41,1,31,pr.中的论述。有学者认为,对该条规则不可能再做其他的解释——它明确地表明了要因主义的立场,因此,罗马法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交付的要因性质,而在于如何理解交付的“正当原因”。[26]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罗马法研究乃至近现代私法研究中最疑难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如下文所述,自中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了非常复杂的原因理论。当学者们对所谓“正当原因”的解释不断趋向主观化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对于要因主义的“原因”的解释逐渐推翻了要因主义本身,从而引出了无因性理论。因而,从原因理论的发展脉络来涤清无因主义理论的路径依赖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何谓“原因”?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民法学上一个重大的难题。在对欧洲大陆法上的原因理论及其演进史缺乏全面、清晰了解的情况下,容易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在笔者看来,现代欧陆民法至少主要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原因”一词——它们相互关联,但却有着不同的内涵,至少可以说它们表述的角度不同。第一个意义上的原因是“契约原因”,它与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契约当事人借助特定的契约关系所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不同的契约类型具有不同的契约原因,例如,买卖契约的原因即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一笔金钱的交换关系。契约的原因可以是典型的(所谓典型契约或有名契约),也可以是非典型的(所谓非典型契约或无名契约)。第二个意义上的原因则是指物权变动的原因,它指的是在特定因果关系上而言的导致物权变动的一个基础关系。例如,就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这一物权效果而言,债权性质的买卖契约恰恰构成了标的物以及价金所有权变动的原因。很明显,在现代法上,契约的原因和物权变动的原因是分属于不同层面上的东西。[27]本文所论及的当然是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也即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作为其“原因”的基础关系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联系表现在:如果法律强调将“原因”(当事人所欲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作为所有契约的要件,那么仅是旨在移转所有权的交付就不可能独立地成为一个契约,因而所有权移转似乎必然要采取要因主义的立场。[28]1.古罗马法学对原因的主要定位那么,古罗马法学家所指的“正当原因”的确切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后世法学家发展出了复杂的原因理论系统,但是对于古罗马的法学家来说,问题似乎没有那么复杂。较为可信的一种看法是:交付的原因存在于当事人间包含了交付标的物的合意的一项交易关系中,例如,当事人间关于买卖的合意即构成了交付出卖物并移转其所有权的原因。由此可见,交付的原因体现在当事人的一项合意之中,而这项合意恰恰体现了交付的经济内涵。因此,如果这种经济内涵包括了物的所有权移转的内容,那么交付就会产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效力,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交付并不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例如,就非要式物而言,以买卖为原因的交付将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如果物的交付是为质权的设立而完成的,那么交付仅产生占有移转(所谓“另状占有”,possessioadinterdicta)的效力;如果因使用借贷的目的而交付标的物,则移转的仅是标的物的持有;考虑到要式物的特殊规则,以买卖为目的的对要式物的交付,则移转的仍然是标的物的占有(所谓“时效占有”possessioadusucapionem)。[29]论及罗马法上“原因”14
的范畴,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罗马法仅将“原因”视为一种具有特定经济内涵的交易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包括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只是隐含在这种原因关系之中,而从未由这种原因关系中被抽象出来。其二,不能将“原因”片面地理解为真正能产生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义务的一个债的法律关系,实际上,任何合法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要包含所有权变动的经济内涵)都可以充当交付的“正当原因”。[30]前述意义上的原因关系有着相当广泛的范畴,而买卖关系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由于罗马法上买卖的特殊性,问题似乎变得更复杂了许多。一方面,在罗马法上存在要式物与非要式物的区分,要式物所有权的移转须以要式买卖(mancipatio)的特别方式来完成,而由于要式买卖的特殊结构,几乎所有的法学家都承认要式买卖是一个典型的抽象行为,所以尽管存在对要式物买卖的“原因”合意,对要式物的简单交付仍然不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在罗马法上,买卖契约具有非常特殊的法律结构——出卖人不负移转出卖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仅承担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并对追夺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31]这样,从逻辑上来说,买卖契约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这似乎与前文对原因的定位有矛盾。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尽管罗马的买卖契约存在上述特殊结构,但这是从法律秩序对契约结构的预设的角度进行观察的结果,其实,当事人在进行买卖时通常当然存有移转出卖物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这可以从关于禁止买卖当事人做出不移转所有权的约定的法律规则中得到验证;第二,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原因”关注的是当事人间一个合意的经济内涵,而非其法律构造。于是,甚至一个不具有契约属性并且根本不产生当事人的交付义务的合意(如赠与)都可以有效地成为所有权移转的原因,而在经济功能上来看,买卖当然意味着商品与金钱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它可以成为出卖物所有权移转的原因。就买卖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即买受人价金的交付而言,情形又有所不同。在罗马的买卖契约结构上,与出卖人不负移转出卖物所有权义务不同,买受人负有交付并移转一笔金钱所有权于出卖人的义务。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金钱的交付要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它是否也以有效的买卖契约作为的其“正当原因”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引导我们进入另一个原因理论——所谓“清偿原因”。2.“清偿原因”(causasolvendi)要全面理解罗马法上对于所有权移转的原因理论,对所谓“清偿原因”的深入探讨是完全必要的。后世的许多罗马法的研究者,常常从所谓“清偿原因”中得出交付系无因的抽象行为的见解。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的确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罗马法的大量文献均表明,在发生“错债清偿”(solutioindebiti)时,“清偿人”所能主张的诉权仅是对人性的返还请求权(condictioindebiti),[32]这似乎意味着,错债清偿同样导致了清偿物所有权的转移。在错债清偿的情形,如果将“原因”界定为实际产生给付义务的债的法律关系,则交付的无因性也就凸显出来了。罗马法学家为满足交付对于“正当原因”的要求,遂将“清偿”(solutio)——而非导致清偿发生的债的关系——本身解释为交付的原因。但是,在笔者看来,在古罗马法学上,“清偿”被作为交付的原因有其特殊的历史性,它与solutio这项制度的起源有关,不能抛开这一历史背景而断言“清偿原因”实际上彰显了无因主义的结构。在罗马法上,solutio最初同要式买卖、要式免除等一样,都是所谓“秤和铜块式”14
的要式行为(solutioperaesetlibram),[33]它是债务人借以使自己摆脱一项同样以要式方法承受的债务的方法。同要式买卖一样,最初它包含了标的物所有权的实际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使得债务约束由于受有对价而解除。因而,在早期罗马法上,solutio本身就完全可以成为所有权移转的“正当原因”,至于通过该要式行为所欲摆脱的那项债务的产生“原因”,由于solutio的要式性,当然对所有权的移转不产生任何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甲通过要式口约(stipulatio)承受了向乙支付10个金币的债务,那么当甲通过solutio的要式行为将10个金币交付给乙从而使自己摆脱债务时,乙的所有权取得的法律上的直接原因是solutio,而非之前的要式口约。因此,即使事后证实了要式口约的无效,作为清偿对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仍然不受影响,因为solutio作为要式行为仍然可以作为标的物发生移转的原因。[34]在早期,solutio所产生的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是绝对的、终局性的,只是到了后来,在错债清偿等情形,才引进condictio的诉权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35]到了古典时期,solutio已逐渐失去其要式性,成为了对dare(以所有权的移转为义务内容)义务予以清偿的一般表述。仍举上述事例,甲向乙交付金币的简单行为(非要式行为)本身就被称为solutio,所以此时的solutio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它不应再继续负担作为所有权移转的法律原因的功能。但是罗马的法学家作为传统的遵从者,在solutio的实质内涵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并未改变原先法律所赋予的功能。[36]这样,当事人之间关于一项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以清偿为目的的合意就可以成为所有权移转效果的“正当原因”了,尽管事实上dare的义务可能根本不存在。然而,即使是这样,在解释上,也不能从其中单独抽象出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并将其作为所有权取得的直接原因。理由之一是,错债清偿导致所有权移转并进而用condictio的诉权来请求给付的返还,其前提是,关于清偿的错误必须是双方的,也就是说,不仅所谓“清偿人”有负债的误信,而且接受人方面也须是善意地误认为自己的确享有债权。如果接受人明知无权受领而接受清偿,则其行为视同盗窃,[37]交付之物的所有权并不发生移转。应该说,在后一种情形,当事人间同样具有移转所有权的合意(尽管接受人方面非出于善意),因此,“清偿”目的对于交付之物所有权的移转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还不能将“清偿原因”等同于抽象的移转所有权的主观合意。而且,即使是摆脱了要式性的“清偿原因”,其作用范围仍然是有限的——交付的“清偿”效力仅针对存在一个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义务(dare)的情形。因此,如果交付的基础不是产生dare义务的债的法律关系,那么就无从将“清偿”作为交付的原因,而只能以一个真实的交易关系作为交付的正当原因。所谓“买卖原因”、“赠与原因”、“嫁资原因”等即属于这种情况:由于买卖、赠与以及设立嫁资本身都不产生移转所有权的义务(dare),因此,只有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赠与关系、嫁资设立关系之时,交付才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38]看来这正是古罗马法学家们对所谓“清偿原因”的定位。应该说,除作为真实交易的普通原因关系(买卖、赠与等)及这种特殊的“清偿原因”外,在罗马法上并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原因关系及理论。后世的法学家,从早期的注释法学派开始,为调和罗马法文献中表面上存在的矛盾(主要是要因交付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原因理论。应该说,许多这样的原因理论实际上并不被古罗马法学家所知,毋宁说它们纯粹是后世法学的创造。所谓“误信的原因”(causaputativa)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3.“误信原因”(causaputativa)14
在未能准确理解“清偿原因”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法学家们在罗马法的文献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即要因交付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矛盾:如果交付的原因是dare的义务本身,那么在该义务不存在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否认给予做出错误给付的人以对物性的所有物返还之诉(reivindicatio)的救济呢?[39]注释法学派的法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体现在它们所发明的“误信原因”的理论之中。根据这种原因理论,所有权移转的原因体现在当事人关于存在一项dare义务的确信之中。“误信原因”在对保罗的D.41,1,31pr.的一段早期注释中就已被注释法学派学者提出。这段对于保罗所论述的“正当原因”的注释是:“正当原因,[可以是]真实的或误信的。如果否认所有权因一误信的原因而发生移转的观点,那么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整章规定(D.12,6)就会与这里所确认的规则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学说汇纂》的这一章恰恰是在标的物所有权因一个误信的原因(exputativacausa)而发生移转时才有适用的余地”。[40]乍看起来,“误信原因”理论并没有多少特异之处,但是它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要比这种最初的印象大得多,因为它为无因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最为重要的一块基石。表面上看,它与前述“清偿原因”似乎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实际上,它完全脱离了罗马法上solutio的特定结构,将产生所有权移转效力与否的衡量要素由客观因素向单纯的主观因素发生了重要的转化。在“误信原因”中,“原因”已经开始向“动机”的意义转化,即只要存在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双方动机,即使发生动机错误(作为行动基础的交易关系不存在),交付仍然被认为具有了“正当原因”。于是,一个原本是要因主义的结构,由于对“原因”的偷梁换柱,已经基本演变成了它的相对面——无因主义。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如一个买卖关系)不存在而当事人认为它存在并因而交付标的物的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则仍然认为标的物所有权发生了移转,那么这个规则体系究竟应被称为无因主义还是要因主义就完全取决于论者对“原因”的界定了:如果将原因定位于真实的交易关系或一项产生移转所有权义务的法律关系,那么显然这是一条无因主义的规则;如果当事人关于存在给付义务的误信亦可被作为导致所有权移转的“原因”,那么它就仍然属于要因主义的范畴。可以说,“误信原因”意义上的“要因”交付理论离萨维尼的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已经相去不远了。[41]Abstract:InRomanlaw,thewilloftransferringthepropertywasn’tcontainedinthenotionoftraditio,theeffectofwhichwascontrolledbythe‘cause’.Atfirstlook,thereseemstobebothelementsofcausaltransferandabstracttransferinthesourcesofRomanlaw.Itsactualreasonis,however,thatthedefinitionsofcausearedifferent.IntheeyesofmostRomanjurists,thetraditio,asarule,iscausal.Duetotheinsufficientknowledgeoftheromanlawnotion‘causasolvendi’,thedoctrineof‘causaputative’waspresentedbytheMiddleAgescholars,makingitpossibletograduallygeneratethedoctrineofabstracttransferfromtheframeofcausaltransferdoctrine.[1]我国民法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多包含在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14
或范围更广的物权变动问题——的研究之中。这一点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萨维尼恰恰是通过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界定(所谓“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而提出了物权契约的理论。惟应注意的是,萨维尼是通过对罗马法上的交付制度(及其在后世的发展)的研究“总结”出物权契约理论的,而这种溯源性的研究恐怕也是我国学者相对较为缺乏的。从罗马法的制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事例见于陈华彬:《罗马法上的Traditio、Stipulatio与近现代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载于《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60页以下。针对该问题的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见于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56页以下(“关于意思表示与原因”标题之下)。另可参见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2]“traditio”这个拉丁词,亦有翻译为“让渡”者,如黄风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的译本中即采此译法(黄风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让渡”一词在中文语义中似有仅指权利的移转之意,而如下文所述,罗马法上的“traditio”有时亦指对物事实上管领的移转,因此还是“交付”的译法更为贴切。[3]例如,在萨维尼的“物权契约”论中,交付当然地具有移转标的物所有权这一要素。有些学者,如彭梵得,虽未直接将罗马法上的交付界定为“物权契约”,但也强调了作出交付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彭氏在其所著《罗马法教科书》中,将交付定义为:“以放弃对物的所有权并使他人接受这一所有权为目的,根据法律认为足以构成所有权转移之依据的关系而实行的交付或给予”,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209页。[4]例如,尤士丁尼《法学阶梯》第3编第14题第3段(I.3.14.3)谓:“……因为,如果某人将物交付(tradit)给疏忽大意的朋友保管,则………”(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本文所引罗马法原始文献资料,除特有说明者外,均由笔者根据拉丁原文(并参照相关意大利文与英文译本)译出。其中,尤士丁尼《法学阶梯》(以下简写为I)据PaulKrueger本,尤士丁尼《学说汇纂》(以下简写为D)据TheodorMommesen本。[5]例如,D.41,1,3(盖尤斯,《论日常事务》第2卷):“我们根据万民法来取得那些通过交付(traditione)而成为我们所有之物……”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基于此,有学者将“交付”直接定义为在主观上包含移转所有权意思的行为。见前注3。[6]指能够发生所有权移转的“交付”。[7]首先,罗马法学家们并不喜欢过分的理论抽象,因此,即使在古典时期,从各个具体的交付——尽管正如后文指出的那样,这个术语本身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了——情形中抽象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也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强调法律行为中“意思”(意志)的因素,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产物。罗马法,作为一个古代法的体系,并不具有“唯意志论”的印迹。一个例证是,尽管罗马法承认一定类型的合意性契约(买卖、租赁、委任和合伙),但是从未承认一个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一般契约概念。[8]有关交付需要具有正当原因的记载最重要的是保罗在D.41,1,31,pr.中的论述:“交付本身从来不移转所有权:它只有与导致其发生的、在先的一个买卖或其他正当原因相结合,才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14
。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2.19、20中也称:“无疑,非要式物可以通过交付而完全归他人所有,只要它是有形的并且因此而可以进行交付。因此,如果我把一件衣服、一块金或者一块银因为买卖或者任何其他原因交付给你,该物就立即变成你的,只要我是所有权人”。关于罗马法是否一律要求原因作为交付基础的问题,见下文。[9]参见[奥]马·卡泽尔:《论交付的正当原因》,田士永译,载于《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10]笔者认为,中世纪法学中关于“名义”(titulus)加“方式”(modus)的所有权移转模式基本符合罗马法的精神。至于在此模式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的理论抽象,包括推翻这一模式的理论,则已经超出了“罗马”的范畴,成为了法学上的创造。有学者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Hugo)就是在其发表的关于名义加取得方式理论的法学论文中提出后来被萨维尼称为“物权合同”的理论的,参见[德]霍·海·雅各布斯:《物权合同存在吗?》,王娜译,载于《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11]持要因说者如MaxKaser(Zur‘IustaCausaTraditionis’,BULLETTINODELL’ISTITUTODIRITTOROMANO,vol.64,1964.);RobinEvans-JonesandGeoffreyD.Maccormack(IustaCausaTraditionis,inNewperspectivesintheRomanLawofProperty,Oxford,1989);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inScrittiinMemoriadiRodolfoSacco)等。持无因论者如PasqualeVoci(StudidiDirittoRomano,Padova-Cedam,1985);MatteoMarrone(IstituzionidiDirittoRomano)等。[12]值得注意的是,D.41,1,36与D.12,1,18pr之间的差异不仅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而且甚至也直接受到了立法者的关注。德国民法典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在论证抽象移转主义之时,不仅引述了萨维尼和温特沙伊德的观点,而且也直接以D.41,1,36来支持无因主义。该立法委员会同时也注意到了D.41,1,36与D.12,1,18pr之间的差异。参见Rolfknütel,VenditaeTrasferimentodellaProprietànelDirittoTedesco,inVenditaeTrasferimentodellaProprietànellaProspettivaStorico-Comparatistica,Torino,1997,p.167.ss。[13]这正是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2,84中所确认的规则,该段条文为:“因而,如果某债务人以一笔金钱向未成年人实行了清偿,那么该笔钱款将为该未成年人所有,但该债务人并不因此而摆脱债务,因为未经监护人准可未成年人不能解除任何债。同样,未经监护人准可未成年人不得转让任何物品。但是,如果他已经由该笔钱款受益,但同时又继续提出清偿的要求,则其要求可能因诈欺抗辩而被驳回”。[14]参见D.46,3,12,4:“即使给付是向一非真实的代理人做出的,只要本人给予了批准,同样也能使债务人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因为批准等同于委任”。[15]D.46,3,58pr(乌尔比安,《论告示》,第80卷):“14
如果某人善意地向一个为他人管理事务之人为清偿,那么他何时能够摆脱债务呢?尤里安认为,在本人对此予以批准之时,他可以摆脱债务。尤里安还问道,在本人予以同意之前,能否据此[对受领人]提起返还之诉?尤里安解答说,应考察做出清偿时行为人的意思究竟是为了使债务人立刻摆脱债务,还是只有在本人批准之后才使债务人摆脱债务:在前一种情形下,能够立刻对代理人提起返还之诉,而在本人予以批准之后,该返还之诉则消灭;在后一种情形,只有在本人不予批准时才能提起返还之诉”。需注意的是,乌尔比安在此根本未提及具有物权请求权性质的所有物返还之诉(reivindicatio),而是一直使用表明具有属人性质的诉权condictio这个词。[16]例如,D.46,3,16(彭波尼,《论告示》,第15卷):“……因为他认为,如果某人承诺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一笔金钱,并在认为该条件已成就的情况下给予了金钱,如果后来条件确已成就,则发生清偿的效果,债务人因此而摆脱债务;该笔金钱在此之前已经成为债权人所有这一点并不构成障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17]参见PasqualeVoci,StudidiDirittoRomano,Padova-Cedam,1985,P.57-58。[18]罗马法上的契约具有典型性,契约的类型是固定的。不属于典型契约的协议(所谓“无名契约”及其他协议)不具有契约的完整效力。关于罗马法契约的类型和典型性的问题,可参见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7页以下。[19]在此,Datio这个拉丁词有特定的法律内涵,它特指标的物所有权发生移转的情形。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Palermo,1999,p.165.[20]例如,D.41,9,1,2(乌尔比安,《论萨宾》,第31卷):“……尤里安认为,如果未婚妻在将物交付给未婚夫时,具有在缔结结婚前该物不归属于未婚夫的意思,则不发生取得时效;但是,如果未婚妻显然不具有该意思,则应认为(尤里安也这样说)该物立即为未婚夫所有……”。[21]在某些情况下,裁判官可能给予做出自己给付的一方当事人以一个事实诉权(以及后来发展出的actiopraescriptisverbis),从而使他能够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对待给付。这种措施属于裁判官法的范畴,它使该种关系最终纳入到所谓“无名契约”调整的范围。无论如何,不当得利的诉权始终都是这种法律关系的典型救济方式。有学者认为,现代法上在契约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有权选择要求履行或解除契约的规定(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453条)的根源即在于对无名契约的这两种保护措施。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cit.,p.505。[22]实际上,论者往往根据自己预先确定的立场而在罗马法文献中各取所需——在实现体系化的过程中删除那些与整体不相符的法源。见费尔根特雷格(Felgenträger)对萨维尼的批判,费尔根特雷格:《冯·萨维尼对所有权转让学说的影响》(1927),第45页,转引自[德]霍·海·雅各布斯:《物权合同存在吗?》,同上,第272-273页。[23]参见PasqualeVoci,StudidiDirittoRomano,cit.,P.61。[24]判断文献的真伪(包括尤士丁尼的“添加”问题)并力图重现罗马法的真实面貌也是后世法学对罗马法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罗马法体系本身是一个变动中的、法源具有多元性的、甚至是时常发生自相矛盾的法律体系,所以不应只拘泥于争辩罗马法的“真正”规则为何,而是要从罗马法学家们对规则背后的合理性的表述中去发现法学的真谛。[25]有关后者,可参见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inScrittiinMemoriadiRodolfoSacco,p.158.nota.5。[26]参见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cit.p.157。14
[27]这两种意义上的原因很容易发生混淆。有关原因理论,其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契约的原因来理解所谓物权变动的原因。例如,有学者在论及法国民法典对于无因主义或要因主义的立场时,引用该法典第1108条(将“适法的原因”作为契约效力的要件)、1131条(“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的债,不生任何效力”)关于契约原因的条款来作为要因主义的论据。虽然契约原因与物权变动的原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所谓无因性理论或要因性理论当然是针对物权变动的原因而言的。以法律对于契约原因的要求直接作为要因主义的论据,并且对两种原因理论之间的相互关联不加以必要的说明,显然有犯逻辑错误的嫌疑。参见上揭陈华彬文,《罗马法上的Traditio、Stipulatio与近现代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第150页。[28]契约之于原因关系的要求,对不同的所有权移转模式的影响方式表现为:在法国、意大利等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例下,契约原因与所有权移转的原因基本合而为一了——一方面,任何契约都必须具有原因,另一方面,具有原因的契约本身就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交付不是所有权移转的条件,而是其结果,并不负担任何意义上的“原因”职能。在要因主义之下,要么坚持契约对原因的要求,不承认交付本身的契约属性(所谓“名义”加“方式”的移转模式),要么如同瑞士法那样,承认交付的契约属性,但是又使其效力与另一个具有原因的契约关系(如买卖契约)发生关联,并以后者作为前者效力的正当性基础。而无因移转主义则彻底放弃了契约对原因的要求,从而使所谓无因契约、抽象契约成为了可能。需注意的是,萨维尼在论述交付的契约属性时并未从契约原因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是在采用了一个新的契约观念的前提下做出交付是一个契约这个判断的。[29]因为,就要式物而言,单纯的交付并不能使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要达此所有权变动的效果,必须由当事人完成特定的移转行为——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30]举例来说,在罗马法上,赠与并不被视为一项契约,甚至它并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充当其他一些典型的法律行为(如要式买卖、拟诉弃权、要式口约等)的“原因”,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cit.,p.585。[31]关于罗马法上买卖契约中出卖人不负移转所有权之义务的问题,可参见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载于《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70年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2月,第424页以下。罗马法文献中的一个典型记载见于D.18,1,25,1(乌尔比安,《论萨宾》,第34卷):“出卖人并无义务使买受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相反,要式口约的承诺人则有义务使要约人取得土地所有权”。[32]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3,91。[33]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3,173、174。[34]关于solutioperaesetlibram的抽象性(无因性),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cit.,p163.[35]关于“清偿原因”与“责任解除历史”的相关性的富有创见的理论,参见拉贝尔(Rabel):《罗马法基础》(第1卷),1915年版,第441页。转引自马·卡泽尔:《论交付的正当原因》,同上,第213页。[36]参见BertholdKupisch,CausalitàeAstrattezza,inLetiziaVacca,VenditaeTrasferimentodellaPropriet14
à,cit.P.185-186。[37]罗马法文献中有许多反映此项规则的记载,例如,D.13,1,18谓:“明知非债而接受金钱者,构成盗窃……”。[38]参见马·卡泽尔:《交付的正当原因》,同上,第226-228页。[39]如前文所述,实际上,在罗马法上,此时的“原因”并不体现在dare的义务上,而是反映在当事人完成某个dare义务的合意中——此项义务本身可以并不存在。这样,在这个原因理论支配下的要因主义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就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另外,尚有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在作为抽象行为的solutio之后才出现的:开始时,只要当事人进行了solutio的要式行为(也许也包括其改变后的非要式形态),标的物的所有权就确定地发生了移转,即使事后证明“债务人”并不真正负有dare的义务,他也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制度(condictioindebiti)恰恰是为了给这种利益失衡的状况提供救济而被发明出来的,因而,两项制度中当然不可能存在根本的冲突,参见BertholdKupisch,CausalitàeAstrattezza,cit.P.186。当然,由于这种特定的原因理论仅存在于罗马法上,在现代法上要因主义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冲突却不能经由类似的解释方法予以解决。[40]这段注释见于13世纪前半期Accurio编纂的一部注释书中,转引自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cit.p.157。[41]国内学者对于萨维尼的理论已有相当详尽的介绍,所以笔者在此不赘述,可参见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第二章),法律出版社1971年;[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第15章《“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以及上揭田士永书《物权行为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误信原因”理论已基本实现了将“原因”转向“动机”的过程,然而,自逻辑层面而言,意思的动机还并非意思本身,萨维尼理论的突破点在于,它最终实现了由交易基础(包括进行交易的动机)向纯粹的移转所有权的主观意思的跨越。在萨维尼那里,罗马法所要求的“原因”被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吸收了。在此笔者想指出的是,了解萨维尼的理论渊源比了解其理论本身要为重要,或者,质言之,只有了解了原因理论的沿革,才可能真正理解萨维尼的理论。这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14